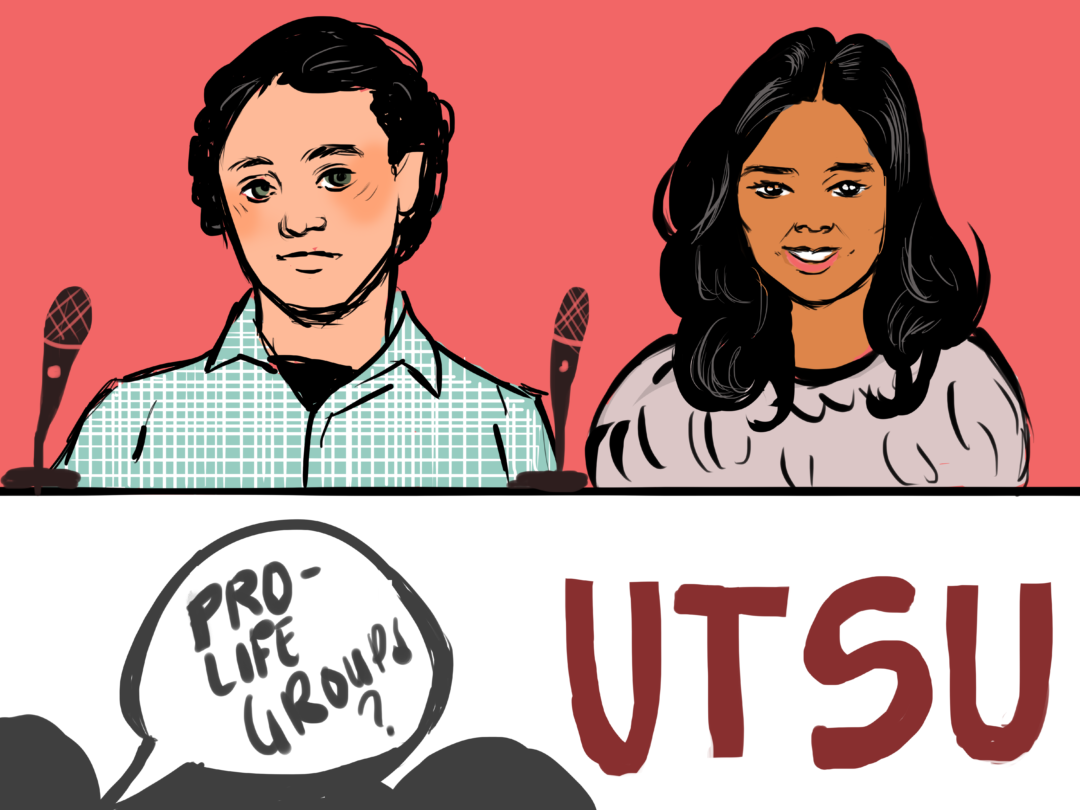在3月21日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TSU)的辩论中,来自Compass队的校园生活副主席独立竞选候选人罗兰达·阿尔法罗(Yolanda Alfaro)和独立竞选人思班塞·罗伯特森(Spencer Robertson)被问及他们对多伦多大学学生会资助有争议社团的观点。给出的例子是一个名为“学生生活”(Students for Life)的社团,一个以图形标志和校园示威为名的、有挑衅性的反堕胎社团。
最终竞选胜利的阿尔法罗给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回答。她坚持认为,如果对社团做出否认拨款的决定,这项决定不是歧视人们的信仰,而是与学生安全有关。
对反堕胎社团的资助问题在被起诉前就已经存在。今年早前,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学生会(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ississauga Students’ Union)被三位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学生生活社团的成员起诉。相似的诉讼是由杜汉学院(Durham College)和安大略省信息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Ontari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反堕胎组织,以及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的 “男性问题”(men’s issues)的社团发起的。另一起有关反堕胎社团的诉讼案件在2016年以瑞尔森大学学生会获胜而告终。
即使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没有法律义务资助某种程度上挑衅、有争议或不受欢迎的社团,它应当采用一种能让广泛的观点在校园中被做为社团来支持的政策。即便是这些观点富有争议或是仅被少数学生接受,也应当如此。
从表面上看,阿尔法罗的回答在辩论中是正确的。她对那些对学生安全构成威胁的,和不受欢迎的团体进行了重要的区分。那些煽动或构成暴力,或者公开针对目标边缘化人群有歧视或憎恨意向的社团,不应被给予资助。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推而广之,所有学生都不应当参与维持这些类型的社团。
当我联系阿尔法罗寻求评论时,她将这种区别模糊到了不存在的程度。虽然她说:“她的立场不是针对有争议的社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对“争议”两字和我持有一样的意见。”但这附加的声明并没有起到作用。对于学生生活社团,她说:“当校园示威发生时,可能对只想安全步行上学的人构成威胁,这是我不赞同的地方。”
阿尔法罗暗示与“学生生活”沟通接触可能危害学生安全或健康。虽然考虑到“学生生活”不会对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但是社团引起关于的原因是他们所表达的反堕胎观点,这些观点已经让许多学生感到不安。
因此,阿尔法罗的观点模糊了“有争议”和“有伤害的”的关键界限,因为这表明,如果观点足够令人不满,表述观点本身就能对学生安全构成威胁。虽然我们需要意识到,有些学生可能会因为学生生活这样的群体而受到不利影响,但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或资助一个群体,就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只要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的职责是支持政治辩论社团,被认为“有争议”不应该成为资助的障碍。首先,有一个阿尔法罗自己也意识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不应该负责决定学生能接触怎样的观点。在校园观点中成为政治观点的决策者超出了副主席的职责所在,并且给予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基于这些观点拒绝资助的能力与开放的话语是不相容的。
广泛被认为不受欢迎的社团或所代表的观点,也不应该成为资助的障碍。即使支持“学生生活”社团的学生比反对的少得多,也不应该成为反对资助社团的理由。广泛的支持或者支持的社团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有前景的社团在被认可前已经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普及: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强制一个社团需要有至少30位成员来得到最少程度的资助。远超于成员名单数量的吸引程度不应当被认同或者考虑资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当认同一个多样化的学生团体一定有多样化的信仰,即使我们许多人并不认同这些信仰,但是他们也应当给予这样一个平台。
假装堕胎不再是一个在校园或在更广泛的加拿大社会有争议的话题。任何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的分歧一定产生远超于“赞成堕胎”或“反对堕胎“的二分法。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希望它得到解决,在政治上这个问题仍然是公开的:在即将举行的省级和联邦级选举中,主要党派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点和投票记录。
公开平等的谈话是建设性谈话,而建设性谈话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意味着要保护“有伤害” 和“有争议”的区别。那些威胁学生身体安全的社团是一回事。但“有争议的”社团在旁观者眼里是很严重的,我们应当确保校园里有不赞同和不受欢迎的观点,以及促进这些观点的学生和社团的存在。
译者注:扎克·罗森是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历史和哲学的大二学生。他是The Varsity时事专栏作者。
翻译/Translate:万春潇/Chunxiao Wan
校对/Proof:钱文聪/Anne Qian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