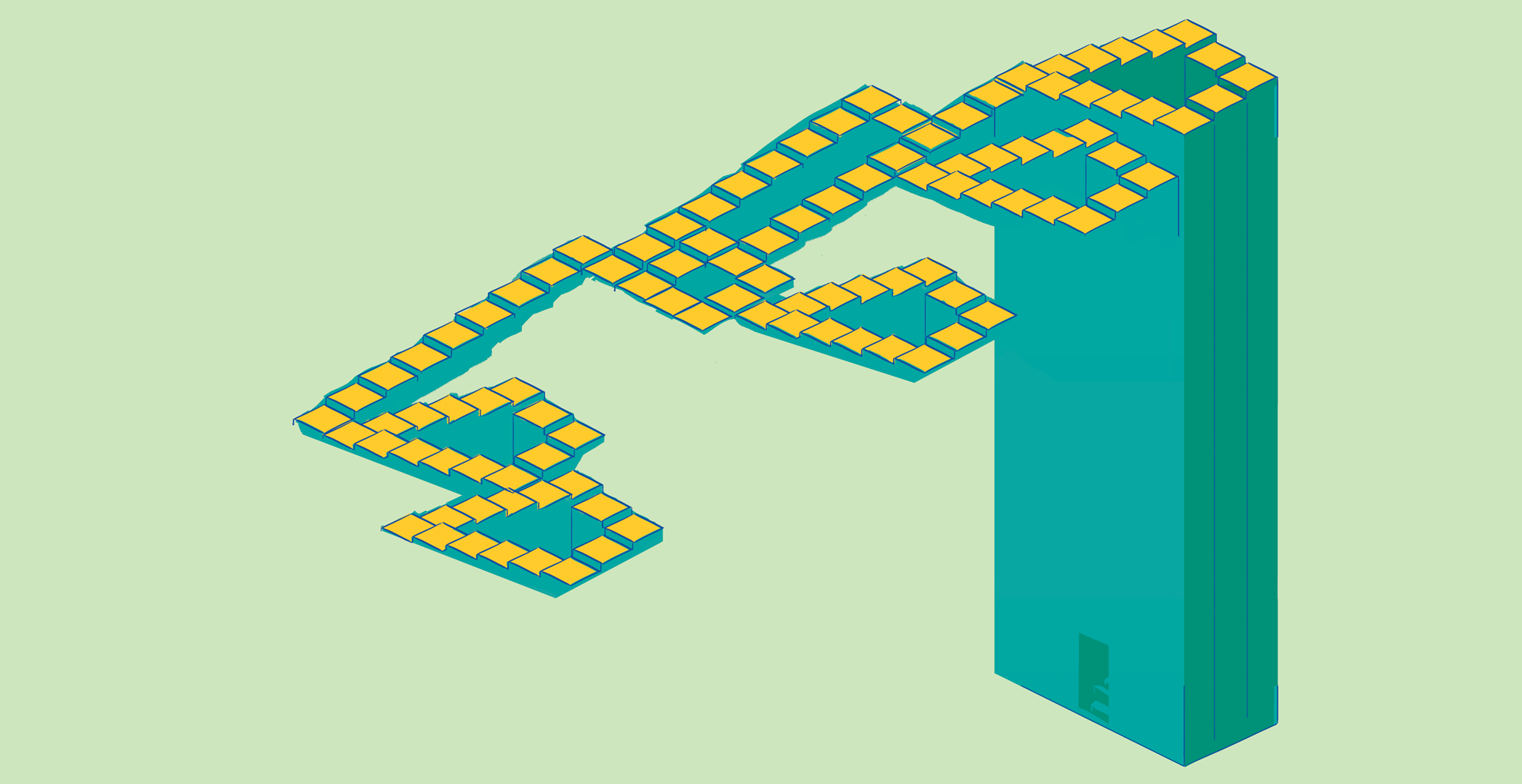内容警告:本文有对自杀及自残的描述
急性焦虑症(panic attack)第一次来袭是独特且难以忘记的。那是2015年在惠特尼厅(Whitney Hall)我自己的房间里。那次经历真的是刻骨铭心的。我记得我剧烈地颤抖着,气喘吁吁、泪流满面,吞下了一片安眠药、两片安眠药、三片安眠药,然后是第四片。我不择手段地摆脱那种感觉。然而,就我所能记住的事情而言,那次侵袭的原因仍然是个谜。
来到多伦多大学
来到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本应意味着我的梦想成真了。我认为它严谨的学术环境能够挑战我的思想、助我成长为一个更强大的人。我住在学生宿舍的目的本应是提高还停留在高中水平的社交技能。我很高兴能认识新同学。我期待将要在这所学校里上课。我曾有一个布告栏,上面钉满了我想加入的学生社团的明信片。
我没有想到我的精神疾病会扼杀我所有的梦想。我没有想到我会变得孤独、与世隔绝——地狱,这一时常闪现的念头让我吓破了胆。然而我还是我,一名编号为1001166285的大一学生,除此之外一无是处。
第一次感到急性焦虑症发作的早晨,我向我的宿舍管理员寻求帮助。我需要一个答案。从六年级开始严重的抑郁就与我形影不离,但我没想到它会跟着我进入大学。在此之前我也从没有真正感到焦虑。同时经历抑郁和焦虑形成了压倒性的循环,我总是感觉我不够出色,并且觉得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想法让我无法得到片刻宁静。
我带着这些想法在我大一的二月份来到了健康与保健办公室 (Health and Wellness office)。我接受诊断、服用药物,并在随后的八个月里维持了相对的平和。
我的大二
就像许多多伦多大学学生一样,我开始感受到居住在多伦多而所要负担的昂贵的生活费。我曾在圣迈克尔学院 (St. Michael’s College) 以半工半读生的身份做过兼职工作,但最终不得不在一家餐厅做第二份工作来维系生计。总的来说,这些在我的正常课程负荷之上每周增加了近25小时的工作时间。
同样,很多学生都知道,这种负担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极端的。
在2015年10月,我患上了一系列健康与保健办公室无法诊断的疾病。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在血检、新处方、核磁共振成像 (MRIs)、CT扫描和新饮食方案之间往复,看看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缓解我的症状。我在睡眠、消化、注意力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这些感觉令人沮丧,害怕且分心。我可以感到我的精神疾病在一点点复发,并变得愈发严重。
到了十一月份,我开始筹划自杀。我觉得我用处方开到的大量药物会让这件事变得很容易,并且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的生活对于任何人还有任何价值。我开始翘掉几乎所有的课程,并借口工作缺席社交活动。我的药物带给了我可怕的副作用,而且反复试验各种药物让我的身体无法适应。我的全部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除了死亡。死亡是唯一一个我觉得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域。
在12月1日,我过量服用药物,这是我生命中第二次尝试自杀。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明白自己已经昏倒在地,并慢慢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了什么。我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他几乎是强迫我去告诉医生。我哭着去看医生,感觉这种强制性的行为是我朋友对我的背叛。我感到羞辱。我很失望这次自杀并没有成功。我希望它能永远是个秘密。
当我的医生听到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被送去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的急救部。在对我的生命体征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之后,我被送进了一个由安保人员守卫的玻璃墙房间。其他患者穿过走廊,通过玻璃与我眼神交流,好奇为什么我会在安保人员的监督之下。我对别人造成威胁了吗?他们担心如果我独自一人,我会逃跑吗?
在西奈山医院等待了六个小时之后,我被送到心理卫生协会(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CAMH)),我被要求在那里至少呆两个晚上。我被迫上交我的全部财物,包括我用来写作业的钢笔,因为他们担心我会用它伤害自己。我还上交了手机,因而我无法与朋友和家人取得联系。在心理卫生协会我见了一系列专家,他们想尽办法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为我提供所需的资源,使其不再发生。经过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孤独和与世隔绝的夜晚,我自由了。
多伦多大学行政部门
我离开心理卫生协会时,已经临近寒假了。我原本计划与家人共度寒假,在新的一年迎接一个崭新的开始。万万没想到的是,返校后,由于多大的行政部门注意到了我试图自杀的行为,我需要处理一系列来自其部门的关切。
我需要重申一次:对有自杀倾向的学生授予离校处理,在多伦多大学已经屡见不鲜了。因为涉及到了类似的情况,教育部的人告知我已经有许多同学声称因曾有过自杀倾向而被大学处以离校。
这一切令我感到十分陌生:我被传唤去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管理人员就我目前的情况谈话。当我进到房间内以后,我被告知大学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我的案件。其中有一个危机顾问和好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企图自杀的事情是怎么传到这么多人的耳朵里的,同时我也对未知的处分充满了恐惧。管理人员与我讨论了停学一个学期的想法,并告知不管我个人的意愿是什么,决定权最后还是在校方手里。
让我气不过的是由一个陌生人来替我决定什么对我最好。尽管她的初心是好的,我还是说服了她让我继续留在多伦多大学。我需要学业和其他公务来分散注意力。我需要朋友,课外活动,以及我热爱的Hart House来帮我分心。幸运的是,我在这场谈判中获得了胜利。但是许多同我有类似处境的同学或许并没有选择和表态的权利。
在那之后,约谈的次数渐渐减少了。我不再是大学监控名单上的一员了。但是同时,我再也不敢贸然向他人吐露我曾有自杀的想法了。
每每想到在心理卫生协会度过的那几晚都令我不寒而栗。我相信那里所提供的服务可以为很多人带来帮助。但当你被迫待在那里的时候,就很难说出这么积极的话了。我想,如果是我自愿去的话,我或许会体会到那些治疗服务给我带来的改善,甚至也会对自己的状况抱有更积极的看法。
2016年3月,我在线性代数的期中考试前夕又遇到了急性焦虑发作。一整个晚上,我都在考虑着自杀。我再一次开始自残,并一整个晚上都蜷缩在卧室的一角。我打算在心理卫生协会一早开门的时候就向他们汇报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我拿到了一个判定我无法再继续学业的医疗诊断。但是我的教授却以我看起来十分健康的理由,对诊断不以为然。若是他看到了几个小时前的我,反应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精神疾病患者已经习惯了用一个微笑隐藏自己的伤痛。甚至可以故作轻松地点点头说一切都好。
媒体
我的故事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有许多新闻媒体的评论或支持,或怀疑我只是想要逃避考试或是吸引人们的眼球。这个故事是通过一系列的发泄性推文(tweet)来推进的。我想让人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知道校园中的体能歧视(对体能或智力较弱的人不去做特别的照顾所构成的歧视)是如何在这些事上具体体现出来的,特别是涉及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不公正案例。我并不是想要特殊的待遇,真的,我甚至没有期望得到媒体的关注或关心。但如果他们联系我,我都回复了,因为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个引起社会对类似事件关注的好办法。
这些经历成为了我校园生活无法抹去的一部分。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正面地表达他们,但这是我人生中宝贵的一课,是这些经历让我彻底改变了处理自己精神疾病的方式。我已经不再将他们视为羞耻深深藏起。这些经历每天都在我做出的大量决定中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得承认——他们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之所以是我的决定因素。只是真正适应他们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
学做学生,更是学做人
我现在是一个大四的大学生。我的医疗诊断被教授拒绝接受之后的这两年,我过的并不容易,但我正在学习处理遇到的困难。我仍然在尝试健康与保健服务,想找到最适合我的治疗方案。我也在尝试各种药物和疗法,并尝试找到最适合我的精神疾病专家。我的一些朋友已经能辨别我发病的前兆并且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回归正常。对此,我永远感谢他们。
对于一个在校生来说,处理精神疾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学生在校园中生活更是尤其困难。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时不时还会缠上我,但是每次想到我的生命还能绽放更绚丽的光彩时,我都成功地压制了它。我现在才二十一岁,这世界还有太多我还没有来得及看的风景,也有等待我去创造的可能性,以及这路上支持我的,给予我爱的亲人和朋友。分享这些故事不仅帮助我走出自己的困境,也提醒人们重视心理疾病患者在校园中的艰难处境——校园对他们不总是那么友好的。据统计,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加拿大人在精神疾病的折磨下苦苦挣扎,情况对于被种族化和边缘化的人们来说就更加严峻。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心里疾病患者。
当然,我仍然是编号为1001166285的学生,我也同时是个有严重抑郁症和自杀倾向的学生。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自己学业和社会关系引发急性焦虑症学生,但我也在努力让这样的情况慢慢变好。我是一个正在学习如何应对这些的学生。我是一个再一次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激情的学生。我虽然每时每刻都在挣扎,但我会继续过好每个明天。
如果你或者你关心的人正为抑郁症或者自杀倾向所困,你可以登录以下网站找寻相关信息和资源:https://suicideprevention.ca/
翻译/Translate: 罗尹聆/Yinling Luo;侯霖/Lin Hou;王佳盈/Sandy Wang
校对/Proof: 管亦笛/Yidi Guan
终校/Final:孙雪霏/ Xuefei S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