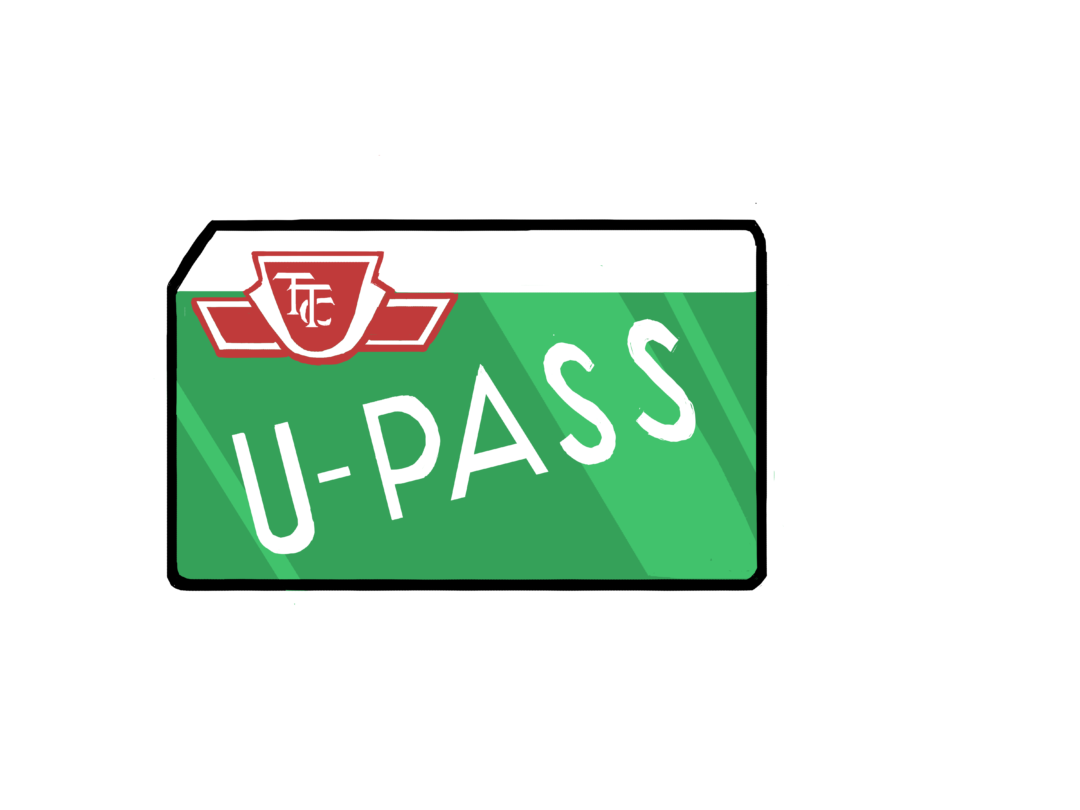致力于持续的跟进,解决漫长的等待时间
善良的朋友、同事和网上的陌生人总是告诉我不应该对于寻求心理健康咨询而感到害怕。但是当我尝试与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UTM)的健康咨询中心(Health & Counseling Centre, HCC)沟通时,我被告知最早的一次预约在一个月之后。作为一个善于掩饰问题紧迫性的高手,我不会强烈要求一个更早的预约。当我见到我的顾问时,引发我精神问题的事件已经过去了,我的感受有所缓解,因为我已经沉迷于我希望避免的不健康和自我毁灭性的应对机制。我在去了许多咨询的预约后只是觉得他们浪费时间,而且我也不需要再回去了。
在我的咨询预约之间有几个月的空白,意味着在这之间出现的感受通常不会在我下次看诊时出现。由于我在开始咨询之前必须填写的广泛电话调查,健康咨询中心非常了解我不稳定的心理健康状况,却在这几个月内从来没有跟进。这只是让我继续推迟预约咨询,因为没有人对我的情况负责任,导致我的精神健康进一步恶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不能参加心理咨询,因为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太差。同时我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持续糟糕,因为我没有参加咨询。
多伦多大学的精神健康服务虽然是可获取的,却不是真正可以被我们所用的。长时间的等待和缺乏辅导预约之间的跟进服务对寻求精神疾病帮助的学生造成了不利。他们让学生沉迷于不健康的应对机制,而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介入。多伦多大学需要通过施行政策来确保咨询师不断与所有报告了精神疾病的学生保持联系,以及为学生提供的辅导员人数应与校园中的学生人数成正比。
译者注:兹哈·勒玛(Zeahaa Rehma)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UTM)大三的学生,主修语言学和专业写作与交流。
修正大学的行动,使其少一些做作,多一些真材实料
学生对校内心理健康资源的有限利用反映了学校缺乏有关治疗的信息和资源。千禧一代的心理疾病率普遍较高,自杀是加拿大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虽然正在采取更广泛的措施来缓解精神疾病并支持精神健康,但这些并不是治疗特定疾病的最佳方法 ——学生通常需要获得专业性的服务。大学提供的关于如何在校内获得精神健康辅助的信息相对较少,而且提供的大部分内容可能都不清楚。
尽管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ro)的主要心理健康网站分享了他们对于治疗精神疾病的愿景和倡议,但关于大学可以为遭受精神健康危机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更像是无用的术语来显示自己的高昂伟大,而不是铺设一条通往让大家拥有健康的思想的道路。
根据我自己需要帮助和接触到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根据我在网上提供的信息制定行动计划。缺乏有用的信息阻碍了我在网站之外寻求更多资源,这最终加剧了我的抑郁和焦虑。
建立更好的心理健康框架有很多复杂性。但是,这个问题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当有人感到困扰时,他们需要别人尽可能的以最明确的方式给予他们信息和资源。在网上张贴错综复杂的报告以保持表象对解决个人经历无用,并且在有人非常需要只因的时候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
译者注:勒哈娜·穆史塔克(Rehana Mushtaq)是因纽斯学院(Innis College)一名大二的学生,主修英语和宗教。
提供基金解决校园内外专业人员的短缺问题
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健康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治疗师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上需求。我们是加拿大最大的大学之一,但不知何故,我们没有足够的医生来为学生服务 ——这是不可接受的。
据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五分之一的加拿大大学生患有精神疾病,如抑郁或焦虑。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字转换为多伦多大学7万名的本科人口,那意味着超过1.4万名学生需要获得足够的精神健康保障。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没有。
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没有家庭医生,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位多伦多大学的医生,他开了一个抗抑郁药来帮助我的焦虑的处方。不过,自十月份以来,我一直在尝试与多伦多大学医疗系统中的治疗师交谈,但一直都没有好转。
如果多伦多大学不想因为未能为需要的学生提供治疗而面临困境——特别是考虑到大学内部产生的压力——他们能做的至少包括提高学生医疗保健覆盖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到系统外寻求帮助。学生生活网站声称,大学健康保险计划(UHIP)可能包括“心理辅导和咨询服务”,但这些服务并未列入UHIP网站或其信息手册中。学生保险(Student Care),这个由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提供的补充健康保险计划,涵盖了一些心理咨询服务——每次资讯高达125美元,每个政策年度最多能进行20次咨询—— 但它们不包括精神治疗,这通常会更贵。
多伦多大学要么聘请更多的辅导员,并为学生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护理,要么应该为学生提供资源,从而让他们到大学外面去治疗。
译者注:艾迪那·海思勒(Adina Heisler) 是一名多伦多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大三学生,主修女性和性别研究以及英语。她是The Varsity学生生活的专栏作家。
消除对咨询会议的反作用限制
心理康复没有时间限制,但多伦多大学针对支持心理健康及解决相关问题的策略是有漏洞的: 在提供的护理数量被限制之后,学生恢复的能力也被限制了。
在遭遇了造成外伤的事件并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双重压力下,我尝试到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健康与保健中心(UTSC Health & Wellness Centre)寻求帮助。虽然我在受助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人都非常友好、很理解我, 但我还是不得不面对学校严酷的健康保健政策——我的学生健康保险计划只会为我提供前八次的治疗。
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个拥有如此卓越的声誉和记录的大学,仅仅简单地把我扔到我的周期治疗计划里——任何人,在处于我这样的身心情况时,都无法轻易接受自己的现状,向专业人员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并且保证在一个规定的日期之前恢复健康。我花了六个月才和我的治疗人员建立起一定的联系,有勇气向他们呢吐露我所经历的痛苦。我并不否认,这些专业人员很有帮助,就像之前那些向我提供帮助的工作人员一样,但让我极其痛心的是,我从一开始就清晰地知道,在八次治疗结束后,我将会被无情的踢走。
通过这件事想让大家知道的重要事实是:对每个人来说,康复的情况都是不同的,特别是心理康复过程。我的结论是,我宁愿花额外的钱来增缴学费和账单、来支付另外的校外治疗,也不愿在创伤未消是就贸然尝试开始工作。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些比我情况更糟糕的人有多么沮丧,特别是那些甚至无法支付额外治疗的学生。
译者注:阿玛拉·默罕默德(Amarra Mohamed)是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UTSC)新闻的的二年级学生
取消对家庭医生转诊的需求
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健康与保健中心(The Health & Wellness Centre at UTSG)向学生提供一系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团体治疗,个人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但在中心的网站上,相关服务流程的具体介绍并未被详细列出。在尝试进一步了解某些可用的帮助服务后,我们能发现,很明显地,获得帮助的过程并不像网站上看起来那么直接简单。
在提供任何实质帮助前,健康中心就要求学生提供家庭医生的提供并授权学校查看此学生的过往病历。尽管这个转诊过程可以由外界医生,或者学校健康中心的员工来完成,这个过程却不能被取代,接待处的人员要求患者必须接受转诊。如果打电话向健康中学求证相关事宜,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这就是学校健康系统的制度,如果没有接受转诊,患者等待接受治疗的时间将会长很多。在作出不接受转诊的决定后,我被转到了更下属的学院,系,部门去继续得到后续帮助。
得到家庭医生的转介许可本来就有很多障碍,大家也都没有必要一定想这么做。比如,如果和一个全科医生讨论心理问题,很容易让人觉得不舒服。健康中心应该考虑不需要中间过程的治疗方案。比如,全天候的现场立时接诊服务可以让学生与已获得许可并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医生进行约谈,然后根据谈话内容制定一个更正式的保健计划。即使这个计划需要学生接受转诊,也应该提供另一种不强制要求接受转诊的选择
译者注:艾敏·沙伊德(Aimin Shahid)是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一名学习英语和写作修辞的学生。
鼓励教授更加理解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灵活选项
从个人经历和其他人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学生们仍然很难向教授证明他们没有明显表征的疾病对他们的功课的影响。简单如上课迟到或未能在规定期限前完成作业之类的事上,即使事先通知了教授,他们的调整要求也可能会受到敌意甚至直接被拒绝。在课堂上,每个人都有责任创建一个更有利于谈论精神疾病的环境。尽管如此,即使许多教授常常会感叹大学生生活的无比艰难,他们仍然不愿意改变课堂上的做法,而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多伦多大学。在著名的教育改革战略中心,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人类学家劳伦赫基斯(Lauren Herckis)发现,相比对自己的教学风格进行必要的改变,坚持熟悉的讲授风格对于教师而言通常是优先考虑的因素。教授们是他们领域的顶尖人物,他们可能很难针对学生的具体问题来讲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具体做法的变化也可以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倾向产生积极的刺激和影响。
比如,教授可以对处理偏离严格时间表的请求其更加宽容。多伦多大学可以,也应该率先尝试为教师提供新的、针对处理精神疾病情况的培训, 就像现有的多元化培训那样。另外,参考专科学院里的辅导员机制,也许我们应该考虑为教师分配更多的辅导员,让学生能够与一些具备他们正在学习的专业知识的人进行交谈,表露自己的心声。现实情况是,没有学生想要落后或让自己的功课受到影响——所以一旦这发生了,一定有一些背后原因。
译者注:艾云·卡尔(Arjun Kaul)是圣迈克尔学院(St. Michael’s College)的一名学习神经科学的大四学生。
对课堂教学进行必要的改变
如果大学想要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质量,也应该考虑一下教室里的问题。考虑到学者们经常在学习生活中产生的压力,我们可以,也必须改变我们施教、学习和评估的方式。
对于初学者来说,教授们应该避免对于学生迟交作业的惩罚。将被扣分的恐惧只会导致他们的压力和焦虑,并没有增强我们的学习效果。这些处罚应该被遗忘和取代。相反,应该和他们协商,尽量错开或自动延长作业的规定期限。
影响最终成绩的平时参与成绩的评估方式也应该被重新考量。平时参与成绩常常并不是很能反映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或平时的付出。相反的,他们反而对于那些平时无法去上课,或者不习惯在人前表达自己的人很不公平。参与分数可以通过更加宽松的方式进行衡量,例如书面反馈或简短的在线测验。
最后,我们还应该允许学生在学期开始和整个学期内与教授谈判教学大纲。考虑到课堂上技能的多样性,学生应该对他们喜欢的作业风格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选择书面作业而不是做展示。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关于如何分配作业重量以及灵活截止日期的选项。这些措施在多伦多大学的课程中并非前所未有的。
其他一些建议还包括制定“从根本改变的”政策,增加“不计分数记学分”以外的选项,进行强制教授检查和反馈会议,在线上传讲座,并让教师组建大班学习小组。这样的变化会改变大学教育学,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应该激励教师调整课程,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和愿望,以防止学习过程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造成影响。
斯坦利·特里维斯(Stanley Treivus)是英尼斯(Innis)学院的五年级学生,主修人类地理学和政治学。
翻译/Translate: 刘星雨/Xingyu Liu, 罗尹聆/Yinling Luo
校对/Proof: 杨典潼/Diantong Y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