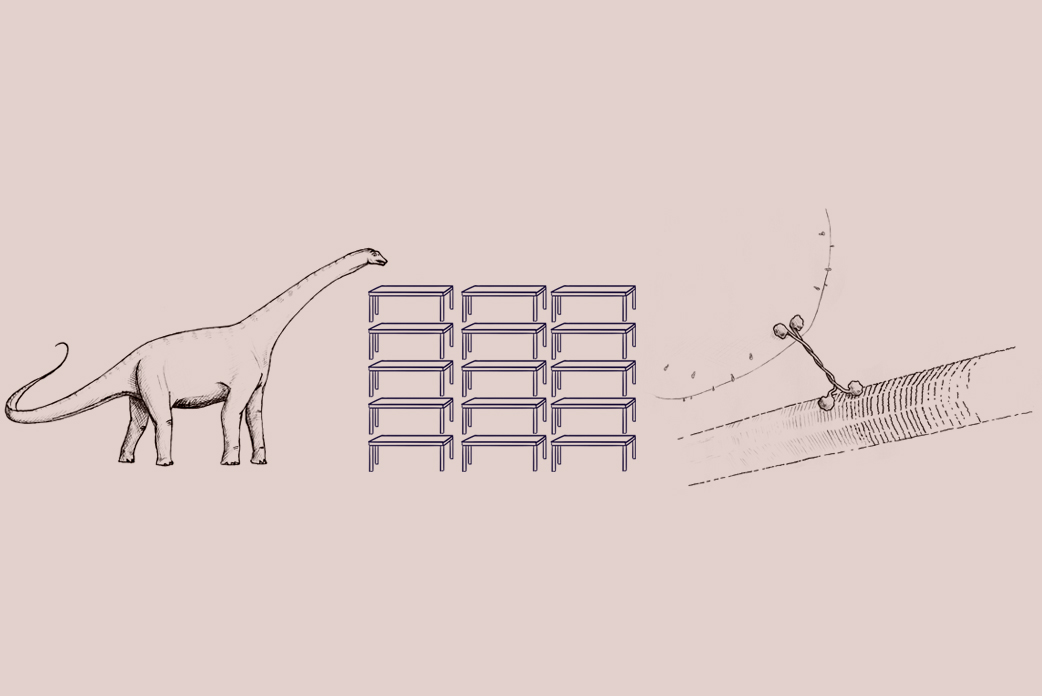在19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R)–它是空间中来自宇宙大爆炸的辐射。在人类的尺度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是一致的,但是通过非常精确的测量,其微小的温度波动被发现了。宇宙学家深入并仔细地研究这些各向异性,以试图了解早期的宇宙。
在一门专题研讨课程–PHY289中,我有幸聆听来自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拉曼・桑德鲁姆(Raman Sundrum)的讲解,他解释了CMBR各向异性的一个令人吃惊的特性:它们的分形性。分形是一个美丽的数学领域,它描述了当放大或缩小时的自相似和相同的形状性质。想想亚马逊河吧—它在拓扑图上蜿蜒蛇行,当经过茂盛的热带丛林时,它的轨迹依然是蛇形的。
更准确地说,CMBR温度的各向异性是随机分形,所以在没有统计分析的帮助下,它们独立规模的一致性是不会显现出来的。然而,在我和桑德拉姆教授进行了核实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CMBR,这个初期宇宙的见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和我们能在地球上发现的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地球上的例子包括春季风暴中闪电的分支弧或贝壳上的兔子轮螺旋。从阿尔罕布拉宫(Alhanbra)的天花板的形状到太空的宇宙尺度,它们在自然中无处不在,围绕在我们身边。
译者注:塔米德・沙菲克(Tahmeed Shafiq)是一名学习数学和物理科学(Mathematical and Physicsal Sciences)的大一学生。
在我修读的一门学习突触神经生物学(Neurobiology of the Synapse)的课程–CJH332中,我了解到,一些研究表明,压力与流感病毒一样具有可传播性。这让我想到了很多次,当我坐在考场的后面考试,看着我面前的每个人时,我的思想顿时充满了压力。
我四处环顾着考场,看着人们使劲挠头,或是离开考场。这种焦虑使我感到非常沉重,以至于坐在考场里这件事比考试本身更加让我感到有压力。
在学习了压力被传播的方式后,我开始坐在考场的前面,因为在那里,我只会察觉到自己。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意外地以积极和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了我的行为,这是一件相当惊人的事。
译者注:查米恩·奈可达(Charmaine Nyakonda)是一名学习神经科学和健康研究(Neuroscience and Health Studies)的大三学生。
生物化学实验室的生活从不会乏味,因为这里有好奇的人、有趣的事实和大量好玩的实验。尽管如此,当你发现爱迪生(Edison)说的“失败有一万种方式”这句话是如此正确时,实验室的工作有时会感觉像是电影《今天暂时停止》(Groundhog Day)里的标语一样:“他正在一遍又一遍地经历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
经过一天漫长的工作后,太阳已经落下,一次失败实验的阴影与月光如影随形,伴着你回家。当第二天醒来时,你意识到自己必须重新再做一次这个实验。但是这一次,你对未来的事情有了更好的了解:对实验计划稍作改进,同时伴随着日复一日的失败–但是成功的希望日渐增长。
这就是学年伊始时我的情况。直到有一天,与窗外暴风雪的黑暗预兆相反,显微镜下一束闪烁的衍射光进入了我的眼睛,这暗示着一次成功–它来自于蛋白质晶体。正如他们所说,在科学实验室中,希望常在。工作中高低起伏常有,而这取决于预期和实验结果。在艰难之时,坚持不懈是生存的唯一途径。
译者注:维伯尔·班达里(Vaibhav Bhandari)是生物化学系(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的研究生。
今年,我有幸上了肯尼思・叶(Kenneth Yip)教授执教的BIO130–一门关于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的课程。而叶教授是迄今为止我在多伦多大学(U of T)见过的最有趣的教授。他有一种教授生物学的方式:一个物体与“无聊” 和“记忆导向”同义–这激励着我去上每节下午6到9点的课。
他的课前的开场白使我们沉浸在对科学的好奇中,并且的确让我们放声大笑。他通过向我们展示有趣的科学广告、俗气的生物学开场白以及有着惊人相关度的模因,解释说科学不仅仅是坐在教室里、记笔记而已。当一名科学家并不意味着你要一直保持严肃。
我最喜欢的时刻是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轻易地解释了纳米技术:“我们用膜将药物或其他物质输送到体内的目标位置—这就是纳米技术!” 这改变了我的生活。
译者注:安雅·蕾卡(Anya Rakhecha)是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系的大一学生。
随着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 ROM)的“周五夜现场”(Friday Night Live, NFL)和安大略省艺术画廊(Art Gallery of Ontario, AGO)“首周四”(First Thursdays)活动逐渐成为受欢迎的派对选择时,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夜店–而我认为,这真的是太棒了。这些活动其实是一些“诡计”—它们以饮料和DJ吸引你去参加,但你最终会为了恐龙而留下。这是我在今年秋季学期修读的一门课程,它向我展示了博物馆的重要性;而最近的这些活动使我对这些机构重拾兴趣。
在修读EEB466—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方式(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Biodiversity)这门课时,我有幸参观了一些在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中非公开展示的藏品。事实上,我在这堂课中学到的一件事是,大多数博物馆标本都隐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尽管这些标本被隐藏起来了,但它们并非无用–事实证明,已死的东西对研究生命极其有用。作为定格了时间的标记,博物馆标本曾被用于研究过去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帮助科学家对当今全球变暖的影响做出有根据的预测。它们甚至曾被用于解开一些谜团:通过对博物馆保存的标本进行测试,发现导致1918年流感疫情的病毒可能并非如我们原本预计的那样,起源于鸟类。
这门课除了让我意识到博物馆的科学重要性之外,还通过展示绝种鸟类标本,以及比我躯干还要大的海洋等足虫标本,让我重新经历了孩童般的惊喜。在一节实验课上,我将一块三亿年前的鱼椎骨放在手心观察 — 虽然它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标本,但它是我对博物馆看法的转折点。
知晓地球上的生命是古老和曾如此繁荣过的这件事是震撼人心的。在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里,参与“周五夜现场”活动的观众在有着数亿年历史的富塔隆柯龙(Futalognkosaurus)(译者注:一种草食性恐龙)标本旁跳舞。我们有责任将它(译者注:富塔隆柯龙标本)保存另一个数亿年。
译者注:克莱拉·泰森(Clara Thaysen)是一名学习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的大五学生,她也是多大校报科学板块的副编辑(Associate Science Editor)。
翻译/Translate: 钱泳欣/Janice Chin
校对/Proof: 吴雯堃/Amy Wu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